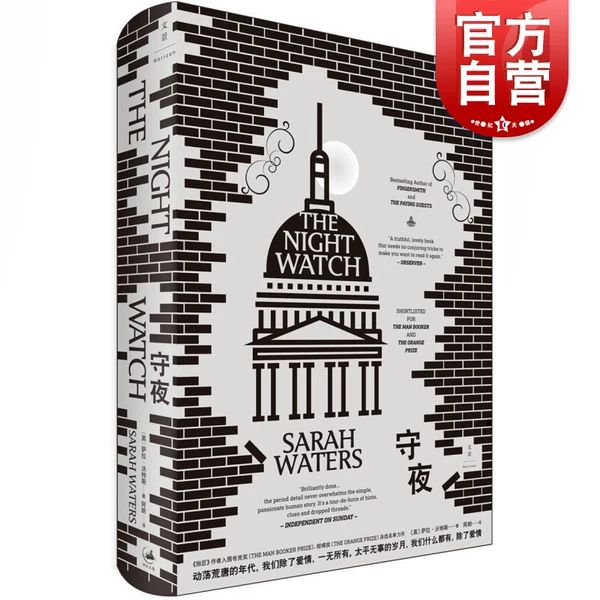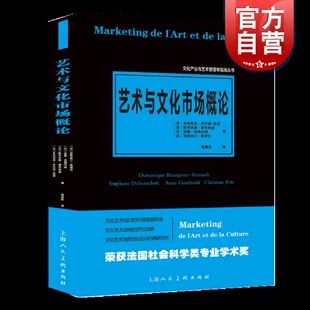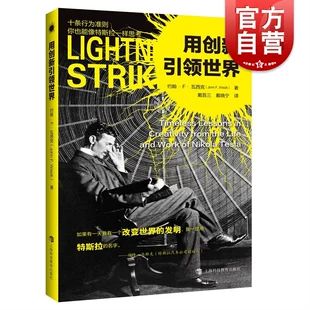守夜 萨拉沃特斯 轻舔丝绒 灵契 指匠 长篇力作 精装 阿朗译本 外国文学 欧美小说 世纪文景
Original saytga havola- 100 — 1999 шт 5000$/donasiga
- 2000 — 50119 шт 4000$/donasiga
- 50120+ шт 3000$/donasiga
1,5$ foto hisobot + tekshiruv
Biz tovarni tekshiramiz va foto hisobot tuzamiz, shunda siz to'g'ri mahsulotni olganizga ishonch hosil qilishingiz mumkin.
Xitoydan Ukraina, O'zbekiston, Yevropa davlatlariga yetkazib berish.
Yetkazib berish, Xitoyda omborga kelganda to'lanadi
Mahsulotlarni qaytarish faqat bizning Xitoydagi omborimizda bo'lganida mumkin. Xitoydan jo'natilgan narsalarni qaytarib bo'lmaydi.
Foto va mahsulot tavsifi

| 产品展示 |
|
|
| 基本信息 |
| 图书名称: | 守夜 |
| 作 者: | 萨拉·沃特斯,[Sarah,Waters],. 著,阿朗 译 |
| 定价: | 59.00 |
| ISBN号: | 9787208155398 |
| 出版社: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开本: | 32 |
| 装帧: | 精装 |
| 出版日期: | 2019-02-01 |
| 编辑推荐 |
|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维多利亚三部曲”《轻舔丝绒》《灵契》《指匠》作者萨拉·沃特斯入围“布克奖”“柑橘奖”决选名单的长篇力作。
★ 战时野蛮、反常、失序,却因世俗的搁置与阶级的碎裂,生出了异样的自由。 ?
★ 抛弃奇情诡计,萨拉·沃特斯笔下四组平凡人的人生遭际也是荡气回肠、牵动人心,足证她仍是“当今英语文坛*会讲故事的作家”。
★ 《指匠》译者阿朗译本,质量过硬,值得收藏!
|
| 内容介绍 |
| 孤行于战后伦敦萧索的街头,凯一身男装,漫无目的。昔日驾着救护车冲锋救世的英雄气概,已随硝烟一同消逝。 供残疾人工作的蜡烛工厂里,邓肯年轻且健康无虞,却理想尽失,生活如一潭死水,直至意外访客把他带回狱中度过的战时岁月。 婚姻介绍所二楼的防火平台上,相对抽烟的海伦与薇芙,每每想敞开心扉,却总是欲言又止。
我们何以落得今天的模样? 这是四个命运交错的伦敦人的故事,由战后的1947年,回溯至1944年,抵达一切开始的1941年。
|
| 作者介绍 |
| 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 1966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文学博士。 三度入围“布克奖”,两度入围“莱思纪念奖”。 曾获“贝蒂·特拉斯克文学奖”、“毛姆文学奖”。 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年度青年作家”(2000)、文学杂志《格兰塔》选为“20位当代*好的英国青年作家”之一(2003)、“英国图书奖”评为“年度作家”(2003)等,文学评论界称其为“当今活着的英语作家中*会讲故事的作家”。
|
| 目录 |
| 正文 |
|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
|
这,凯对自己说,就是现在你落得的模样:一个手表和钟都停顿,靠着看拜访房东的残疾病人来知道时日的家伙。 她站在打开的窗前,穿着无领衬衫和浅灰色内裤,抽着一支烟,望着伦纳德先生的病人们来去。他们都到得很准时——准时得她可以根据他们来知道时间。驼背的女人,星期一十点来,受伤的士兵,星期四十一点来。星期二下午一点来的是位老人家,由一个毫无烟火气的少年陪伴。凯喜欢观望他们。她喜欢看他们从街上慢慢走来。老男人的深色西装整洁,像殡仪员,男孩耐心、严肃、英俊,他俩仿佛就象征着青春和衰老,凯觉得,就像斯坦利·斯潘塞之类讲究的现代派画家画笔下的人物。在他们之后是一个女人和她的儿子,一个戴眼镜的瘸小孩。再后面,是一位患风湿病的印度女人。瘸小孩的妈妈跟伦纳德医生在门厅说话的时候,他有时会站在门前的小道上,用他的大靴子蹭起路边的青苔和土。最近有一次,他抬头看见了正在往下望的凯。那会儿,凯听到他在楼梯上闹别扭,不肯自己去上厕所。 “你是怕门上那些天使吗?”她听到他妈妈说,“天哪,那只是画啦,这么大的孩子了还怕!” 但是凯猜到,吓着他的肯定不是伦纳德先生那些爱德华风格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天使,而是可能会撞见她。他肯定以为她是阁楼幽灵,或是疯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对的。有时候她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就像疯子一样。有时候她又静坐着,几个小时都不动,比影子还静止,因为她看见影子都在地毯上缓慢蠕动。她觉得自己真的像幽灵,她已经变成这房子渐渐褪色的一部分,融入阴影中,而阴影就像灰尘一般,在这栋房子里以各种古怪的形态存在。 火车在两街之外驶过,驶入克拉珀姆交汇站,她感到手臂下的窗框传来火车经过的震动。她肩膀后方的灯泡突然亮了,闪了两下,好像在眨眼睛,然后又熄灭了。壁炉里的煤渣——这是个丑陋的小壁炉,这房间原先是用人的房间——轻轻地塌了下来。凯吸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拧灭。 她在窗前站了一个多小时了。那天是星期二,她见到一个单侧手臂肌肉萎缩的塌鼻子男人来了,她似乎在等,等那两个斯坦利·斯潘塞的画中人。不过后来她决定放弃。她决定出门去。这天天气晴好,九月中旬的天气,战后第三个九月。她穿过房间,回到隔壁那间她用作卧室的房间,开始换衣服。 房间灰暗,几块窗玻璃没有了,伦纳德先生用了油毡布来密封窗户。床很高,床上铺着快磨平的灯芯绒床单。这床会让你不愉快地想到,多少年来不知多少人在上面睡过,他们在上面做爱、出生、死去,或在发烧中辗转翻腾。床散发着微微的酸味,就像一双久不换袜的脚。但是凯已经习以为常,不闻其味了。这房间对她来说,不过是一个睡眠之处,或者卧而无眠之处。墙上还是她搬进来时的样子,空无一物、乏善可陈。她没挂任何一张照片,或放任何一本书,她没有照片也没有书。在一个角落里她拉了一条线,线上挂着木衣架,衣架上挂着她的衣服。除此以外,她几乎什么都没有。 至少,这些衣服很整齐。她挑了一双做工精良的袜子,几条裁剪合身的长裤。她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那是一件软领的衬衫,衣领处的纽扣可松开,是女式的。 但她的鞋是男鞋。她用了一点时间把鞋擦亮。她别上银袖扣,然后梳了梳褐色的短发,抹上一点头油使头发更齐整。走在街上,若不仔细看,人们常常以为她是个清秀的后生。她经常被年长的妇女称作“年轻人”甚至“小伙子”。但是,如果他们仔细端详她的脸,立刻会看见岁月的痕迹,会发现她的白发。其实,下一次过生日,她就整整三十七岁了。 她走下楼梯,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以免惊动了伦纳德先生。但是,要在嘎吱作响而且凹凸不平的楼梯上悄悄走很不容易。她上了厕所,然后在洗手间花了几分钟洗脸、刷牙。她的脸在光线下显得有点绿,因为常春藤几乎完全遮盖了窗口。水管里的水先是堵了一下,然后喷溅出来,热水器旁边挂着一支扳手,碰到水完全堵住的时候,就要拿扳手敲敲四周水管,让它出水。 洗手间旁边,就是伦纳德先生的治疗室。即便是在刷牙,洗脸盆里水声哗哗,凯也能够听到他那激动而音调单一的声音,他在给那个手臂萎缩的塌鼻子男人治疗。她从洗手间出来,轻轻走过治疗室门口时,那单调的声音变大了,听起来就像某种机器的震鸣。 “埃里克,”她听到他说,“你得——哼哼——。怎么能在——哼嗡——重新完整时——嗡嗡——?” 她轻手轻脚下楼梯,拉开没有上锁的大门,在门阶上站了一会儿,几乎是犹豫了。天空的白亮让她眯起了眼。天突然变得了无生气,与其说晴好,不如说是干涸、乏累。她觉得自己能感到灰尘正在落到她的唇上、睫毛上、眼角里。但她不想回去。她必须对得起那梳理好的头发、擦亮了的鞋,还有戴好的袖扣。她走下门阶,开始行走。她像一个目标明确的人那样走着,仿佛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虽然,实际上,她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人可访。那一天,跟她的每一天一样,都是空无。她认真地走出每一步,好像脚下的大地正随着她走的每一步,从空无之中生出来。 她往西面去,穿过被战火摧毁、废墟已清扫干净的街,朝着旺兹沃思方向走去。 “今天贝克上校不在啊,霍勒斯叔叔。”邓肯和芒迪先生走近这所房子,邓肯抬头望着阁楼的窗户说。 邓肯有些失落,他想见到伦纳德先生的租客。他喜欢她大胆的发型,她男式风格的服装,还有她那轮廓分明、与众不同的脸。他觉得她可能做过女飞行员,或空军妇女辅助队的中士什么的,换句话说,她是那些战时曾欣然冲锋陷阵、战后被冷落在一旁的女人中的一员。贝克上校是芒迪先生给她起的外号。他也想看见她站在阁楼的窗前。听到邓肯的话他抬头望望,点了点头,然后低头继续走路,喘得没法说话。 他和邓肯是大老远从白城来到拉文德山的。他们走得比较慢,得换乘巴士,中间还得停歇休息。一来一去几乎得用去一整天时间。邓肯每周二全天休息,然后周六加班来补上。他工作的厂里的人对这很支持。“这孩子对他叔真是尽心尽力!”他听到他们这么说,不止一次。他们不知道其实芒迪先生并不是他的叔叔。他们也完全不知道他从伦纳德先生这儿接受了什么治疗,可能他们以为他去了医院。邓肯无所谓他们怎样想。 他带芒迪先生走到这栋有些歪斜的房子的阴影下。邓肯觉得,这房子看起来最吓人的时候,就是当你走进去,被它的阴影笼罩时。它是这附近唯一剩下的房子,战前这里曾是一长排的联排屋。它两边的墙上都仍有污痕。两边的墙曾经连着邻居的房子,现在只剩些若隐若现的楼梯拐角的印迹,以及那些不复存在的壁炉留下的凹陷。邓肯想不出是什么支撑着这栋房子屹立不倒,他总是无法消除心中那一丝恐惧,他怕某一天他和芒迪先生走进去,关门时稍微用力,这房子就会崩塌。 所以他轻轻地关门,关上门之后房子就显得正常了。门厅比较昏暗沉寂,靠墙摆了一圈硬靠背椅,一个没挂衣服的衣帽架,两三盆无精打采的植物,地上是黑白花纹的瓷砖,有几块脱落了,露出下面的灰色水泥。瓷灯罩是漂亮的玫瑰色,本来应该是用来罩煤气灯的,现在它罩着一只连在胶木插座上的电灯泡,灯泡吊在一根已经磨损的褐色电线上。 邓肯会注意到这些瑕疵和细节,这是他的生活乐趣之一。他们到得越早,他越高兴。到得早,他就有时间先扶芒迪先生在椅子上坐下,然后静静地在门厅走走,细看周围物件。他欣赏转角精致的楼梯栏杆、颜色晦暗的黄铜梯级包边。他喜欢柜子门上一个已经变了颜色的象牙把手,还有护墙板上的油漆,油漆曾被篦刷过,以使它看起来更像木头。通往地下室的走廊尽头摆着一个竹制桌子,上面有一些俗气的摆件,在那堆石膏猫狗、镇纸、马略尔卡陶土花瓶之间,有他最喜欢的一样东西:一只古老的彩绘碗,上面画着美丽的蛇和水果图案。伦纳德先生在碗里放了些核桃,核桃上蒙着灰尘,上面还有一对铁制核桃夹子。邓肯每次靠近这碗,都忍不住从骨子里感到一阵灾难性的小小震荡,那是他想象中,有人拿起那夹子然后不小心滑落,砸在瓷碗上激起的震荡。 碗里的核桃今天看起来一切如常,但是久无人动,上面的灰尘仿佛起了毛。邓肯也仔细端详过屋里的几幅画,它们歪斜地挂在墙上。这房子里的东西都是歪斜的。画都是些平庸的作品,用的是普通的牛津画框。但是它们也给他带来愉悦感——一种不同的愉悦——就是那种注视外貌平平之物的快感:你不是我的,我才不要你呢。 楼上传来一些动静,他敏捷地走回芒迪先生身边。门开了,他听到说话声,那是伦纳德先生送那个年轻人走,那人每次都在他们前面。邓肯也喜欢见到这个人,几乎和他喜欢见到贝克上校和彩绘碗一样,因为那人阳光开朗。他也许是个水手。“还好吗,伙计们?”他对邓肯说,并挤了挤眼睛。他问了问今天的天气,又问了问芒迪先生的风湿病,边问边从兜里掏出香烟,放到嘴里,掏火柴,点火。所有动作都单手完成,干净利落,另一只发育不全的手就垂在身体一旁。 邓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还要来看医生,他这样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了。他想,可能那年轻人想要一个爱人,当然了,手臂有问题,姑娘们多半是不喜欢的。 那年轻人把火柴盒放回兜里走了。伦纳德先生领邓肯和芒迪先生上楼。当然,他走得很慢,将就着芒迪先生的步子。 “好烦啊,”芒迪先生说,“让我爬这破楼,到底有啥用?” “好了,好了!”伦纳德先生说。 他和邓肯扶着芒迪先生进了治疗室,把他安置在一张硬靠背椅上,脱下他的外套,让他舒服地坐好。伦纳德先生拿出一本黑色的笔记本,打开瞟了一眼,然后正对芒迪先生,在自己的硬椅上坐下。邓肯走到窗前,在窗边一个包了垫子的矮箱上坐下,把芒迪先生的外套放在大腿上。窗子挂有网眼帘子,挂在一根绳子上,有些下垂,散发出某种苦味。这房间的墙上是拷花墙纸,上面过了一层有光泽的巧克力色漆。 伦纳德先生搓了搓双手,问道:“说说吧,从上次见面之后你感觉怎么样了?” 芒迪先生低下头。“不是太好。”他说。 “还是有痛的念头?” “我摆脱不掉啊。” “但你没去用那些虚假的治疗手段吧?” 芒迪先生有点为难地扭了扭头。“这个,”过了一会儿他承认,“就是一点阿司匹林吧。” 伦纳德先生沉下脸看着芒迪先生,仿佛在说真是的,真是的。“好吧,你自己很清楚的,用这些虚假方法同时又求助于精神疗法的人会怎样?他就像被两个主人往两边拉的驴,哪儿也去不了。你知道的,不是吗?” “可就是,”芒迪先生说,“太痛了啊——” “痛的感觉!”伦纳德先生带着一点被逗乐的神情和极大的蔑视说。他摇了摇椅子,“这椅子要承受你的重量,它痛不痛?怎么不痛啊,用来做椅腿儿的木头,不就像你腿上的骨头和肌肉吗?你说承受着你的重量的骨头和肌肉在痛,但是没人说椅子腿儿痛,因为没人相信木头会痛。只要你不相信你的腿会痛,那腿的痛就能被忘却,就像你不觉得木头会痛一样。这你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芒迪先生乖乖地说。 “你知道,”伦纳德先生重复道,“好,那我们开始吧。” 邓肯纹丝不动地坐着,在治疗过程中保持极度安静和静止不动是必须的。尤其是现在,当伦纳德先生集中念力,集中动力,集中思想,好去对抗芒迪先生假想中的风湿痛。他微微向后仰头,聚精会神地向前望,却不是望芒迪先生,而是望向挂在壁炉上方的一幅画,画中是一位眼神柔和的女人,穿着维多利亚式高领长裙。邓肯认得,那是基督教科学派的创始人玛丽·贝格·爱迪女士。黑色画框上,有人——可能就是伦纳德先生自己——用瓷漆写了一句话,笔触不是很顺畅。那句话说的是:在思想的大门前,随时做个搬运工。 这句话每次都让邓肯想笑。不是因为他觉得这话有什么滑稽,而是因为在这种时刻笑,好像特别可怕。他总是在这种时候开始感到恐慌,他还要坐那么久,需要那么安静,他觉得自己肯定会发出点声响,弄出点动静——比如跳起来啊,突然尖叫啊,倒地打滚啊什么的……但为时已晚,此时伦纳德先生已经换了个姿势,他身体前倾,紧盯芒迪先生。当他再次开口,换成了一种全神贯注、充满迫切和自信的耳语。 “亲爱的霍勒斯,”他说,“你必须听我说,你那些关于风湿痛的念头都是虚假的。你没有风湿。你没有痛。你不会受到那些想法的影响,那些想法认为疾病和病痛是事物的规则和条件……亲爱的霍勒斯,你听我说,你无所畏惧。没有什么回忆能吓唬到你。没有什么回忆能让你相信不幸还会重来。你无所畏惧,亲爱的霍勒斯,爱与你同在,爱在你身边,充盈四周……” 这些话不停地继续——就像一阵雨,像严厉的爱人一阵温柔的敲打。邓肯觉得——他现在早忘了想笑的念头——邓肯觉得在这番话下,不可能不交出自己,乖乖地听话,不可能不接受训示,被感动,被说服。邓肯想起那个手臂肌肉萎缩的年轻人,他想象他坐在芒迪先生现在坐的椅子上,被告知“爱与你同在”,被告知“你无所畏惧”,不停的念想自己的手臂长出来,长出来,肌肉渐渐丰满。这可能实现吗?邓肯希望能实现,为了芒迪先生,为了那个年轻人,邓肯愿意这样想。他非常希望它能实现。
|
 .....
..... .....
.....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
 Nigeria
Nigeria